
 (楊詠裕攝影)
(楊詠裕攝影)
決定權真的在女孩身上嗎?我們一起思考
文/黃郁晴
「這次機會真的很難得,不只話題性高,藝術性更是不用擔心。妳要是再不決定,我們只好考慮別人了。」青春只有一次,女孩陷入憂慮與焦慮,自己到底該不該「為藝術犧牲」?
在我的教學現場,有人提出這個情境,在場的年輕學子紛紛沉重地點頭,表示對這樣的要求感到困惑。
決定權在女孩身上,為什麼整件事卻讓女孩這麼痛苦呢?女孩開始失眠、冒痘痘,想到必須美美的,壓力就更大——怎麼好像藝術還沒誕生,犧牲卻已經發生了呢?會不會有可能,從頭到尾決定權都不在女孩身上?
轉念一想,決定權確實是在女孩身上的。只是女孩們太習慣把他人的課題放在自己之前,努力達成他人期待而忽略自己的感受。其實轉身離開也是一種選擇,機會不會只有一次,藝術首先存於安好的身心。
你就是你自己的《藝術之子》,希望這樣的訊息能透過這部劇本,傳達給正深陷迷惘的人。
●●●●●●

羞恥的尺度——陰道的度量衡
文/李姿穎 ab
世界衡量女人羞恥感的方法,來自於預設男性為標準值的尺度,語言文法的陰陽性、藝術文化的正典、醫療科學的研究方式⋯⋯,畢竟在女性貞操帶問世有骨灰級之久的至今,尚未發明男性貞操帶。有些事值不值得說,總得看這把尺如何斟酌。
好比說,除了與女性器官互動的動作本身,這世界似乎不太搭理子宮與陰道的事,大約 50% 的女人會罹患子宮肌腺症或子宮肌瘤,但鮮少人知道其中差異。何況是幾乎所有女性一生中至少得過一次的陰道炎與尿道炎。在此斗膽向各大怡提倡 DEI 的企業建議,推動陰道炎假,實為進步體現。
陰道炎這種病,理應列入假別。月經來潮或季節變化,陰唇如同被蟲蟻咬噬般痛癢,又陰道彷彿提掛 5KG 啞鈴的沉重,行走間步步驚心,何況是夜晚輾轉難眠。尿道炎也是種睡不著病,女人尿道相較於男人短小,因而更常與尿道炎直球對決,尿頻尿急一晚起來八百次不說,排尿時的灼熱與刀割感,下腹部疼痛腫脹如爆破氣球。那癢抓了又抓,於是陰唇滿佈傷口,結痂生恨。
這一枚不潔不淨的疼,俗稱羞恥。我們確實很難在談正經公事時說,不好意思,我下體癢到快死了,得去一下廁所。究竟什麼是微小的事?那齧咬般的體感貫穿女人的身體,成為身體暗啞的歷史與創傷。資本主義以羞恥感製造威脅,無處不是「讓妹妹白拋拋幼咪咪」的清潔保養廣告,接著安麗「7分鐘淨白透」「讓男友驚呼的少女粉」「緊緻彈性,老公高興」,女人的陰道繼續接招,那難以啟齒的暗沈傷口,如何在這少女粉的貞節牌坊裡驗明正身?
把被世界丈量為「羞恥」的身體經驗,寫進《不道德索引》裡,不過是重新校正量度女性的尺。將人們以為不足掛齒的傷痕與死透了的記憶,不斷驗屍與指認,將惡臭觸目攤在陽光下,指出疼痛所在位置,重建刻度、立下新的基準點,也是重建女人作為人類的尊嚴。把那把丈量裙子與陰莖長短的尺,用來探測恥的深度。
●●●●●●
 (陳佩芸攝影)
(陳佩芸攝影)
女孩當自愛
文/劉芷妤
從還是孩子開始,絕大多數的女性就被要求自愛。玩沙的時候雙膝距離太遠,領口低了一些,裙襬高了一點,跟男生說話的時候甩了一下馬尾⋯⋯幾乎每一件事情,都會得到一句苦口婆心意味深長的「女生要自愛一點」。
然而幾乎每一回,他們說的「自愛」都不是字面上的意義,背後的意思其實是「自限」,把「那裡」和「那裡」藏起來,盡可能地不要被任何人留意到你的性別。不會有人挑明了說「那裡」是哪裡,也沒人說清楚不自愛會怎麼樣,但女孩們就是下意識地知道不能問。
悲傷的是,最為奮力要女孩們自愛的,經常是她們的母親,她們曾經也在不確定自愛到底是什麼意思時,驚恐地自愛著,再把同樣的驚恐傳遞下去,那是代代相傳的創傷,每一次傳承,都讓女性的卑微更根深柢固一些。
以至於,總被嚴厲要求自愛的女孩們長大之後,總是像《女神自助餐》裡〈荔枝使用說明〉的隸芝那樣,千辛萬苦地,想要從層層綑綁的「自愛」之中,找到一點點真的可以愛自己的餘地。
●●●●●●

性暴力是一種結構——那麼,在創傷修復的過程中,什麼才是真正重要的?
文/王曉丹
性暴力並非現代社會的產物,而是深植於人類歷史數千年的行為模式,長久以來鑲嵌在文化、親密關係與不對等權力之中。因此,性暴力不只是個人的偏差行為,它更是一種結構性的不平等社會狀態——我們身處其中,渾然不覺,卻往往都在與這個結構協商,以自身的主體能動性回應結構。然而,正是這種無所不在的結構,其中的主流話語強化了加害者的權力,操弄著「正常與異常」、「同意與強迫」、「善意與惡意」的二元邏輯,在灰色地帶中製造模糊與傷害。
也因此,許多人在這樣的結構之下,會產生困惑與自我懷疑:
「這個人說這樣的話,真的算是騷擾嗎?他是出於善意,還是別有用心?」
「會不會是我太敏感了?只是誤會一場?」
當受創者無法辨識自身經歷是否構成侵害,他們往往只能依賴主流話語來詮釋自己的經驗。這樣的過程,不僅使受創者與自己疏離,更可能讓他們在反覆的社會協商中,最終懷疑自己的感受,進而否定創傷本身。
《真相與修復》透過多起真實個案的敘述,引導我們進入受創與修復的細節現場,迫使我們思考:對受創者而言,什麼才是修復真正需要的?真相究竟是什麼?在整個修復的歷程中,最重要的,不只是還原事件的客觀經過,更是在權力不對等的世界裡,如何讓受創者重新與自身經驗連結、重新建構其主體性與尊嚴。
●●●●●●

從孵蛋器變回人的那天——其實關於我的身體,你們可以直接跟我討論。
文/葉佳怡
有時你以為自己沒傷口,但其實是沒機會癒合。
高中時出車禍,在醫院時,只是被母親拖來的父親突然提出一個跟醫生說明毫無關係的問題,「她還能生嗎?」
大學時卵巢檢查出巧克力囊腫,醫生說,「這個通常生了會好,不用處理。」我說,「我沒有要生。」醫生立刻轉頭望向我的母親,繼續向她解釋我的病情。
研究所時去複診,因為疑似囊腫滲血造成腹痛,醫生說,「等要懷孕前再來開刀,反正這個之後還會長。」我說,「我沒有要生。」醫生轉頭繼續跟我身邊的男友解釋病情。
工作十年後,我去看醫生,此時兩邊的囊腫都好大了。我盯著醫生的眼睛,「我沒有要生。」我決心不再讓醫生別開眼神。
我開刀拿掉囊腫,吃藥進行治療。那種藥會讓人難以懷孕,我說沒關係,「我真的沒有要生。」
我終於被治好了。
●●●●●●
 (林昶志攝影)
(林昶志攝影)
不准哭?為什麼流淚需要資格?
文/郝妮爾
我過去有很長一段時間不敢哭。當時在做一連女性暴力倖存者的田調過程,社工坐在我的旁邊,受訪者坐在我正前方。密閉房間中的一個小時,我一直跟自己說:「不准哭。」誰都可以哭,但就妳不准哭。倒不是因為覺得哭出來就輸了,或者眼淚「太女生」,而是認為我沒有掉眼淚的資格,我需要強悍地接住她們所有的經歷,才能客觀地寫下,我需要公正而無私地把我所感受到的紀錄下來。直到某次我終於忍耐不住,看著對方的雙眼——擊中我的不是誰的眼淚,而是對方眼底的明亮。受傷的人也可以很明亮,書寫的我也可以再軟弱一些。後來我每次都是哭著走出那座小房間,不想再去思考流淚需要什麼資格。大概也是從那時候開始,我也開始相信,「把一件事情好好說出來」不必任何資格,甚至無關乎Timing。
現在,就是最好的時間。成為自己,就是足夠完整的資格。
●●●●●●
 (陳佩芸攝影)
(陳佩芸攝影)
你是女神,為什麼不能幫我寫推薦函?
文/陳育萱
身為長年在男校任教的女老師,印象深刻的是學生口中總有那麼一、二位校園之花。在他們口中,同齡女孩往往不夠美,個性不夠好,話鋒一轉,進入社會工作的年輕女性,就理所當然成為某些學生口中的「女神」。
我以為女神是被奉以鮮花香火的。直到一次,某個導師班學生向我憤憤提及,他「特地」去找曾為班導的女神老師「寫推薦函」,慘遭拒絕。
昔日導師的拒絕無可厚非,學生的怒意無非是「女神」的作為,已不符合想像中能配合一起拍照打卡,宛如偶像般能事事滿足粉絲。
他的失望不過是曾深埋於心的厭女情結,不小心在升學制度中被自己血淋淋揭開罷了。我在班上播了《誰先愛上他的》,我猜他需要泥塑的是小王或小三這兩尊,就送給他向內在陰性與陽性能量和解的祭改電影。
●●●●●●

為什麼還是被框起來了?
文/廖瞇
以為自己不怕老,卻發現那是因為長得年輕,視覺年齡永遠比實際年齡小上十歲還要更小。所以不是不怕,只是因為長得小。為什麼人怕老?女人更怕?怕老怕胖。怕的背後是什麼?是你要被喜歡就要有被喜歡的樣子。什麼健康就是美那是對別人說,但自己就不行,自己就是要年輕要瘦,要看起來好看。不想承認但就是這樣。那解方是什麼?解方是承認自己在框架內,看見自己的框,發現自己仍在無形中被框起來,被眼光框起來,被社會框起來。
我當然可以喜歡自己是什麼樣子,但那是因為我喜歡,而不是因為別人喜歡。這有時很難分,它們互相交纏。收到花會很開心,但要會採花給自己,不是等人送花給你。推《始於極限》 ,上野千鶴子與鈴木涼美的書信對談,她們跨越了社會習以為常的「邊界」,讓人看見自己思考的邊。
●●●●●●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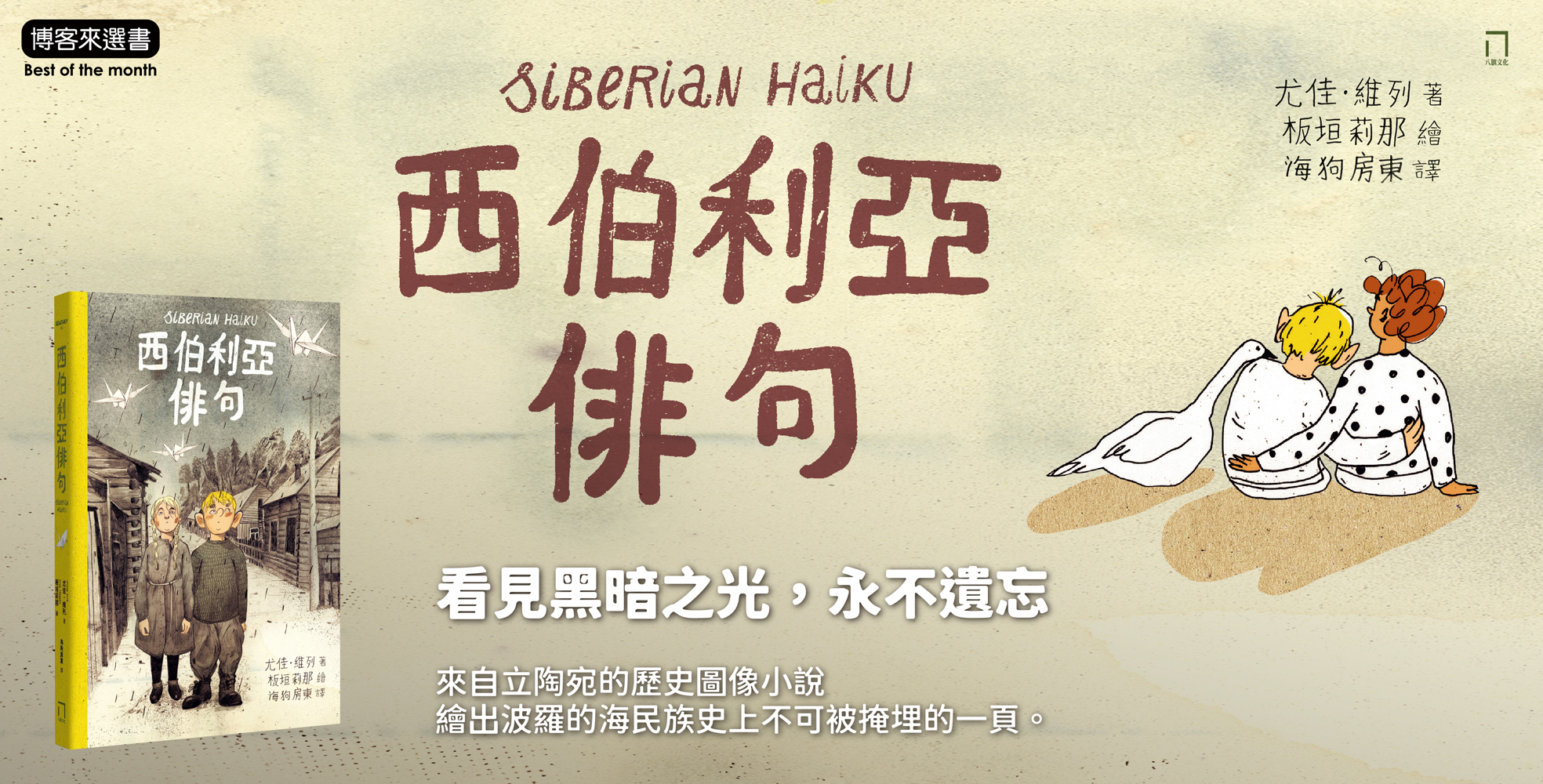






回文章列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