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王曉磊(筆名:六神磊磊)曾任記者,自2013年起以「讀金庸」系列文章廣受好評,其後將獨到視角與深厚學養轉向唐詩,掀起一股新的唐詩書寫風潮。他擅長還原詩人的喜怒哀樂、掙扎與困惑,讓現代讀者在千年前的詩句中得到強烈共鳴。
《唐詩光明頂》是王曉磊「唐詩三部曲」的第二部,深入盛唐時代。有別於學院派的嚴謹考證,王曉磊將唐詩融於生活,以幽默風趣的筆觸,顛覆我們對「詩仙」、「詩聖」的刻板印象。他筆下的李白、杜甫不是遙不可及的文化符號,而是有著現代人焦慮與掙扎的「普通人」。這種寫法,讓唐詩變得鮮活而富有生命力。
本次專訪,我們特別邀請王曉磊暢談《唐詩光明頂》的創作緣起與核心理念。他分享如何從小與唐詩結下不解之緣,又如何在閱讀中尋求心靈的慰藉;他將剖析屈原對唐朝詩人的深遠影響,更以張九齡的人生起伏為例,為「躺平世代」的年輕人提供實用建議。
來跟隨他的腳步,感受那穿越千年依然擲地有聲的詩歌力量: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Q=新經典文化編輯部 A=王曉磊 (本書作者)
Q:請問您攻讀了唐詩多久,才能寫得這樣融會貫通?
A:談不上「攻讀」,從小到大除了看武俠小說,陪我最多的就是唐詩。陪伴我最多的一本書叫《唐詩三百首新編》,是馬茂元、趙昌平兩位老師編著的,幾乎天天帶著。上大學的幾年,因為高考沒考好,心情一直比較壓抑,也是唐詩給我很多解脫。
大學假期裡有一次回家,在書店裡,遇見一大一小兩個小孩。大孩子對小的說:「你都果大(這麼大)了,還看唐詩啊。」這個事印象很深。說明很多小朋友覺得唐詩是很幼稚的,是兒歌、順口溜。相信如果他看了《唐詩光明頂》,會覺得哪怕自己再長大,也可以讀唐詩的。
Q:繁體版出版剛好是端午前夕,您寫過屈原是許多唐朝詩人的偶像。您認為屈原影響唐朝詩人最重要的是什麼?
A:三個,「我好美」、「我好氣」、「我好軸」。「軸」現在是說一個人死板固執鑽牛角尖。這個是屈原的「靈魂吶喊三句」,是後來中國詩歌的「原始碼」。後來唐朝詩人的靈魂吶喊都是這三個。
「我好美」,就是對美好的不懈追求和無比自信。他覺得自己就是最美的,他用自然界好多美的東西來形容自己、裝飾自己。「我好氣」,就是對不公正的憤怒,始終保持憤怒;「我好軸」,是對自己節操的堅持,永遠不妥協。
到陶淵明,原始碼慢慢多了一個,「我好想得開」。
Q:您提過「唐詩通向當下」。想請教:唐代小鎮出身的詩人張九齡的人生起伏,可以帶給「躺平世代」或「低薪高壓」的年輕人怎樣的啟示?
A:一個是活得久一點。
張九齡活了六十多歲,算不錯的了,人生才能幾落幾起。你如果活太短了,落一下就沒了,起都起不來。把身體搞好最關鍵。好比李白有個故事,唐代宗初年,據說想拜李白做左拾遺,結果李白已經去世。代宗即位的時候李白恰好過世。如果李白多活一兩歲,可能就趕上了。
時代你改變不了,但可以改變你的身體。你自怨自艾,不喜歡你的人最開心了。不要讓他們開心。
二是手邊總會有可以做的事。張九齡不被朝廷喜歡了,回到家裡,可以修大庾嶺路。後來貶到荊州,寫了很多好詩。我們可能做不了這麼大的事,那可不可以做一點小事。讀一本書,錄一段影片,寫一則小故事,不可能什麼都做不了。
Q:很多讀者喜歡您在書中所寫的李白、杜甫等詩人,跳脫傳統「詩仙」、「詩聖」的框架,貼近現代人的焦慮與掙扎。是什麼讓您能夠不用傳統文學史「造神」的寫法?您寫唐詩的真正動力是什麼?
A:其實傳統文學史恰恰倒沒有「造神」,或者說有人推崇就有人挑剔。你看《舊唐書.杜甫傳》,那個杜甫很跋扈的。那麼多年的文學批評史,李白、杜甫都被讚揚,但是也被挑剔的。王夫之就很不喜歡杜甫。
「造神」厲害的恰恰是現在,比如網上,很多人覺得這個不能碰,那個不能談,如果談了好像就傷了他的面子。我說李世民的詩哪些不好,立刻有網民生氣:「你也配談李世民。」
「詩仙」、「詩聖」,我寫的時候會平視他們,看到他們的種種矛盾、糾結、痛苦。要先知道他們也是凡人,才能更了解他們的偉大。
Q:從「北固山下的小舟」開篇到「杜甫病故的小舟」收尾,這種「船行喻史」的結構是刻意的嗎?用意是什麼?
A:是有意的,從小舟開始,從小舟結束,是一個歷史的循環。王灣的小舟飄來,「潮平兩岸闊,風正一帆懸」,那麼光明、開闊,就是盛唐開始了;杜甫的小舟飄過,「百年歌自苦,未見有知音」,就是盛唐落幕了。
有個趣事,第一篇「一艘小舟飄開的盛唐序幕」,有編者說「飄」不對,船是不能飄的,要改成「漂」,後來拿出南北朝《與朱元思書》的「從流飄蕩,任意東西」,你看古人的船就是可以「飄」的,才終於過關。
Q:才剛讀完《唐詩光明頂》,編輯們已經在期待笑忘書。預計會何時寫完出版呢?
A:說好的是明年年初,但現在看來不行了,我希望上半年可以出。我很頭疼,因為一本書裡包括中唐、晚唐,要寫的詩人太多,還不知道怎麼辦。
延伸閱讀
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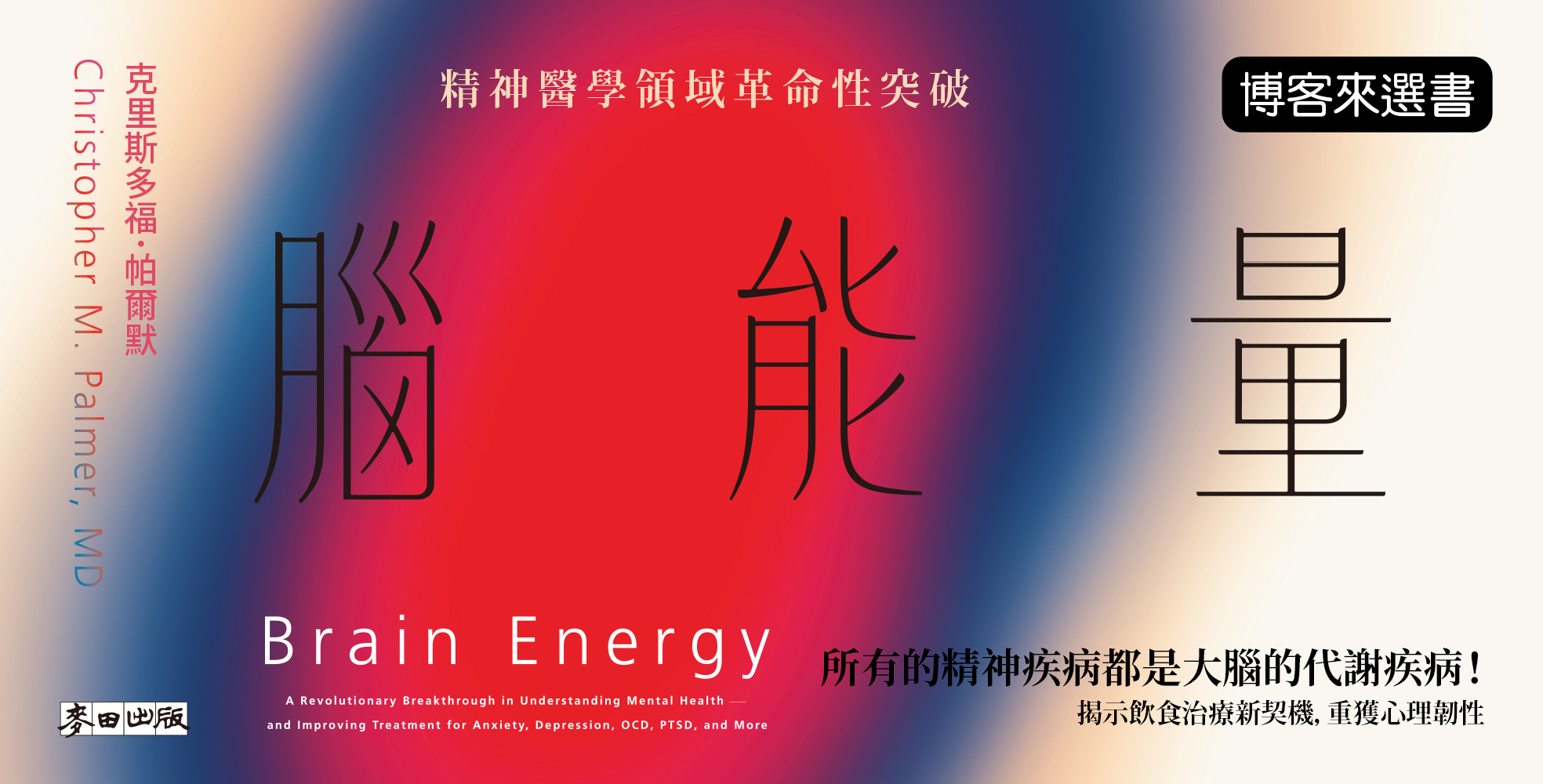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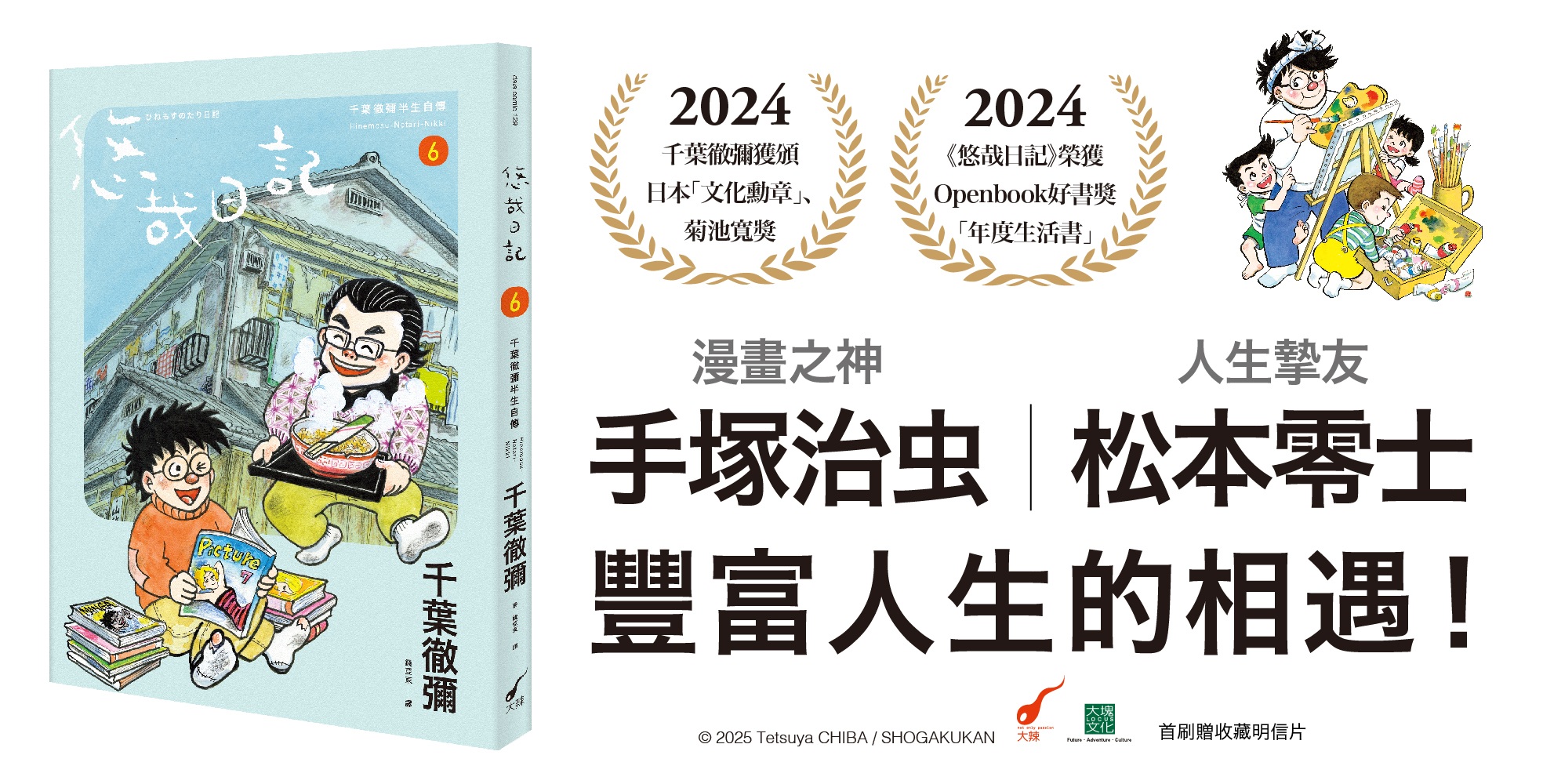

回文章列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