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人工流產,是許多女性人生中無法言說的一章,許多故事,被藏得太深太久,連最親密的人也從未得知,也鮮少成為創作的主題。因此,當游擊文化2023年買下《她們的選擇:關於人工流產,作家們想說》繁中版權,同時想製作一本「台灣版別冊」以補足該書缺少的台灣案例,邀吳曉樂推薦可收錄哪些作品時,她想了又想,只想到胡淑雯2006年的小說〈墮胎者〉,基於一股不甘心,原本輕薄短小的別冊計畫,在吳曉樂的統籌主編下,擴展成文學形式多元、內容扎實厚重的專書《以為無人傾聽的她們》。
一開始,吳曉樂就希望不只是收錄作品,還要納入人工流產經驗者的訪談,身邊不少友人都訝異極了。有人直言:「一定做不起來。」沒想到,徵求受訪者的問卷一釋出,竟收到兩百多則回應。「很多人不只是勾選選項,還在最後備註欄寫了好多話。就算有人最終沒被選為受訪者,仍是希望自己的故事被知道。那份熱切,不只是大家想講,也包括大家想找一個可以說的人。」這是一種對吳曉樂、對游擊文化的信任。吳曉樂說,「我們沒有什麼爺爺的名聲可以賭,但我們願意賭上自己的名聲,好好處理這些故事。」
不只訪談故事,這本書更有詩、小說、劇本、歷史研究、法律面與醫療面。「我心裡想,一定要有當代的作品,不能永遠只提到胡淑雯二十年前寫的〈墮胎者〉,我們要有更多文本產生。」於是,吳曉樂從年齡相仿的創作者中邀約,不只對方要願意書寫人工流產題材,更希望她們不是因為私交,或抱著疑慮勉強答應。
巧的是,找上作家張嘉真、徐珮芬與鄧九雲,她們第一時間的回信都是肯定的,其中徐珮芬甚至表示:「這個題目我想寫很久了。」
創作者陣容到齊了,新難題仍接踵而至。鄧九雲寫的是一齣獨幕劇,原本是為了讓不習慣閱讀文字的觀眾,有機會接觸這個議題;然而鄧九雲提醒,劇本與書中其他文類並置時,整體閱讀的節奏與完整性可能會出現落差,讓讀者感覺有些跳脫。吳曉樂說,「既然劇作家提出的是一個無法忽視的顧慮,那麼,讀劇會就非辦不可了。」
因此,書出版後也要辦一場讀劇售票演出。原本已經分身乏術的編輯團隊,根本難以負荷劇場籌備與行政作業。所幸,有行銷企劃夥伴詩韻即時加入團隊。從前總是蒙著頭寫作的吳曉樂笑說,「在這次歷練後,我覺得自己好像變成青年創業家。」
即便是她擅長的書寫,也在這次遭遇重挫,「我寫的第一版訪談,被出版社打槍到血肉模糊。」吳曉樂說,「訪談過程中,受訪者會談到家庭的問題、伴侶的對待,甚至是自己沒得到媽媽的愛。現代人或許知道『母愛創傷』、『情緒勒索』這些詞,但有些人講不出來,而這些情緒與委屈,最終都在傾訴『人工流產』的回憶時傾瀉而出,有些受訪者會突然崩潰大哭。我常常會愣在現場,想著:我現在該扮演什麼角色?」

讓吳曉樂最震驚、意外的,是在問卷備註欄寫著「在密醫那裡做人工流產」的妮婭。
年僅二十多歲的妮婭,怎麼會跟「密醫」這個古老辭彙有關?吳曉樂好奇詢問妮婭:從14歲在學校學到性教育,到進行人工流產的時間差為何?妮婭回答,「沒有『中間』的時間點。」因為她在14歲時被補習班老師性侵。
那是一場初秋在高雄進行的訪談,咖啡店裡冷氣再涼,也能感覺到秋老虎的威力,但吳曉樂的腦袋瞬間當機,「我想著完了完了、我毫無心理準備,該如何在不造成負擔的情況下拋出問題?」也有其他受訪者註明人工流產是因為被性侵,而妮婭是到了現場才告知。吳曉樂先坦承自己不知所措的心情,原本話少的妮婭自然地繼續說了下去,讓訪談順利進行。
吳曉樂說,「讓我感到難過的是,妮婭目前看似一般的過生活,但她習慣用抽離的方式看待自己。妮婭在二十歲讀到《房思琪的初戀樂園》,房思琪有愛上老師,可是妮婭沒有,她知道自己就是被暴力地對待了,而且被老師帶去給密醫做流產,父母始終以為女兒那天只是去補習。」
「在寫下這些人的故事時,我刻意把自己拉到非常後面,因為每個人的生命張力都太強烈了,強烈到我覺得——吳曉樂應該在文章裡藏起來,只要忠實呈現故事就好。」但團隊編輯提醒,讀者不會只想讀一則則悲傷或戲劇化的故事,也會想知道吳曉樂的觀點:她在這當中是怎麼想的、她扮演什麼角色?於是,第一版初稿被退了。
當時交稿後,吳曉樂剛開啟一趟歐洲旅行,心裡卻滿是交戰。一方面對於得大幅重寫難以接受;另一方面也明白,書要出版,內容得經過更多沉澱、處理,編輯必須對讀者負責。
返程時,吳曉樂第一次搭商務艙,原本12個小時的高空舒適體驗,她拿來瘋狂改稿。受訪者從未對任何人說的壓抑與記憶,被她以「吳曉樂在聽」的方式重新寫出來。「我可能是世界上唯一完整知道她們發生過這些事的人,這份沉重,比我過去寫的任何小說都難下筆。」

大家對非虛構寫作有很高的信任,但這種信任有時也成了一種限制——彷彿一件事情「真的發生過」,才值得被關注。但有時候,人是可以再往前走一點點的,不一定非得「真實發生」;透過書寫,人可以捕捉某種抽象的經驗,那也是真實的一部分。
因此當吳曉樂請馮議徹設計書封時,特別要求:「不要直接畫一個女性的身體。可否以一些色塊呈現?彷彿代表一個人原本的位置,但中間又彼此連結。」這樣的設計,就像書中鄧九雲的獨幕劇〈正常父母〉,故事不一定真的發生過,卻能觸碰到某種生命經驗。
「如果太依賴真實的力量,可能讓沒有相關經驗的人覺得,又不關我的事。」吳曉樂說,「所以我們想把視角往上拉一點。書裡提到的情感與狀態,曾經發生在某人身上、某段人生裡,以某種形式存在過。這種模糊地帶,可以讓人多想一點,再靠近一點。」
在眾多訪談中,有些人帶來了截然不同的價值觀。像是受訪者世景,一開口就說她早忘了做過人工流產。對照其他人心中難以釋懷的結,這樣的輕描淡寫顯得格外特別。但吳曉樂知道,必須更細緻地描寫這個案例,以免引起「不釋懷就是自己不夠灑脫」的誤解。
不過,世景的現身是重要的。早在胡淑雯的小說〈墮胎者〉裡,主角的姑姑就是這樣的角色——她直白地說「我拿過孩子」,然後話題就結束了。這次年紀最大的60歲受訪者麗詩,也是相似反應,當年她因為要出國進修,選擇終止懷孕。但多年後麗詩才發現,當時的男友、如今的丈夫,其實對這件事耿耿於懷。

吳曉樂說起對「流產」這個詞最初的印象,是小時候無意間聽到大人在說某人「拿過小孩」,大人雖然講得隱晦,卻又坦然得像在說一件平常事:「不然怎麼辦呢?」不只是童年回憶,吳曉樂讀國中時,一位朋友的媽媽意外懷孕,還開家庭會議投票該不該生,最後孩子還是生下來了。後來朋友帶著妹妹出門時,會直率地告訴大家:「這就是那個小孩啦。」
但長大後,吳曉樂發現那份坦然不見了,罪惡感變得龐大起來。也因此,編輯團隊決定將歷史的觀點納入本書。人工流產的罪惡感,與兩個時間點密切相關:一是日本文化中的「嬰靈」概念在1980年進入台灣,二是基督教勢力在台灣的興起。這些因素讓人工流產在之後的二十年間,變成一件難以啟齒的事。吳曉樂希望透過書籍的出版,推動社會討論,恢復原本那種平凡、坦然的狀態。
尤其,隨著當代的孩子有了上網發聲的能力,開始反駁「窮有窮的養法」這句話,他們形容自己是「天崩開局」(人生的競賽一開始就非常不利),這顯示文化又轉了一個彎。越來越多人不再相信「小孩帶財」,也不再說「生下來就知道怎麼養」,而是明白:如果不該生或不想生,就真的不要生。
這樣的思維轉變,不全是因為社會更加尊重女性的身體,而是開始尊重「孩子不想活得那麼辛苦」的權利。「生」這件事,不再是偉大的象徵。身為父母,別再自我感動了——養一個孩子,需要金錢、體力與意識上的覺悟。
編輯團隊也陷入書名的苦思:要直接出現「人工流產」嗎?畢竟,人工流產在書中的篇幅,比想像的少,反而更著重於討論:人如何看待生育?女性一生會經歷哪些階段與掙扎?女性從出生到老,承受的一切究竟有多沉重?
籌備時,他們從書名開始重新對焦,如那些受訪者說的:「這件事,只有你知道得最完整。爸媽不知道、丈夫不知道、朋友也不知道。」尤其是美夏說的:「每個人都像一本書,有些回憶我們草草翻頁,不忍細讀,但為了這個採訪,我重讀了被自己跳過的段落。這件事,終於不用帶進棺材了。」美夏許願,以後再提到人工流產,大家可以理解為「一個過日子的普通選擇」,女人就是把日子過下去而已。
吳曉樂說,幾乎所有受訪者都提到同一件事:這個社會很習慣開空頭支票,但她們卻真正思考過自己是否有能力履行承諾。書中這些女性的故事讓吳曉樂更加明白,「若要討論終止懷孕與否的選擇,必須鑲入女性的一生,做整體的檢視,沒有一個選擇是容易的。」

延伸閱讀

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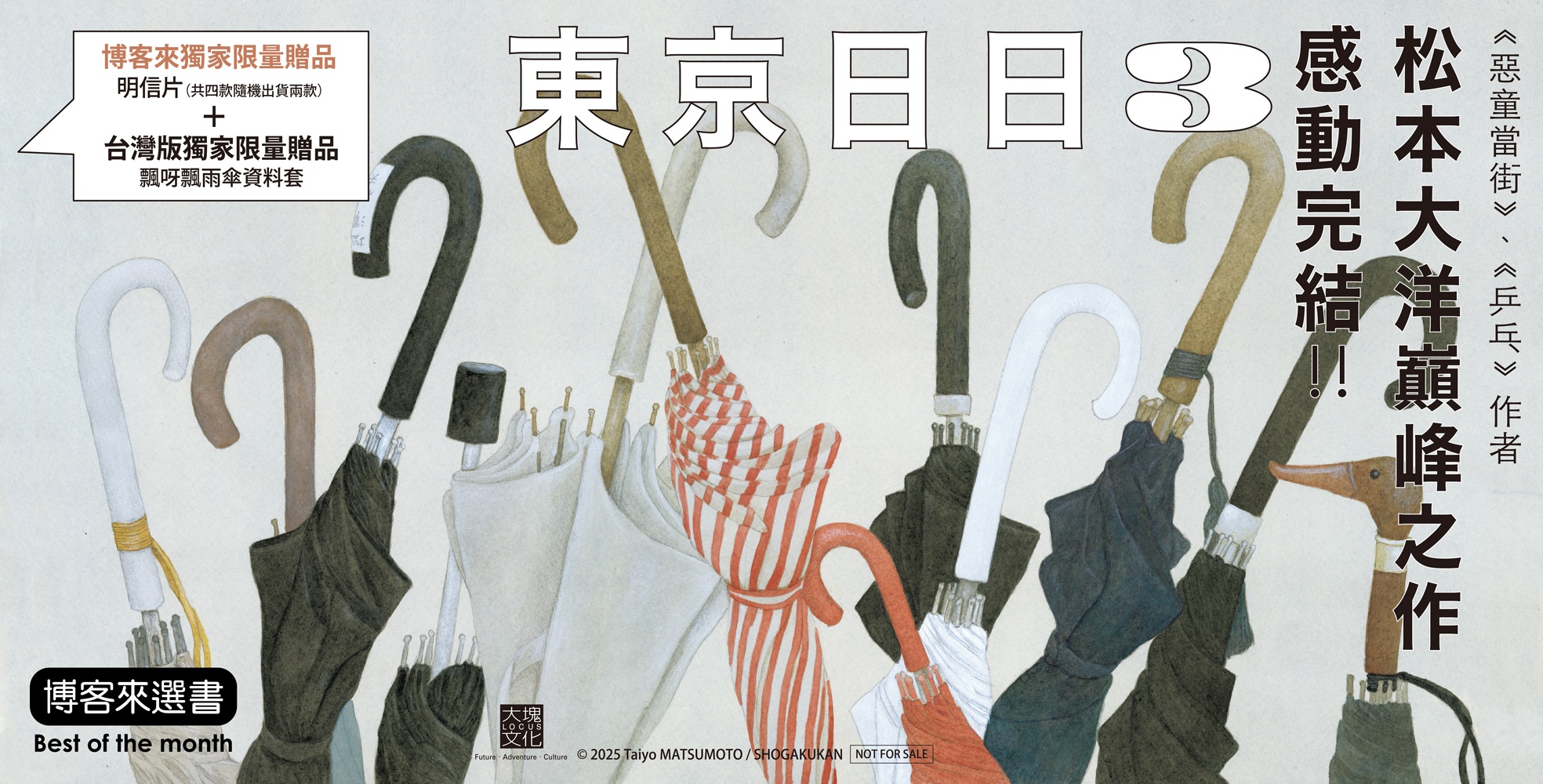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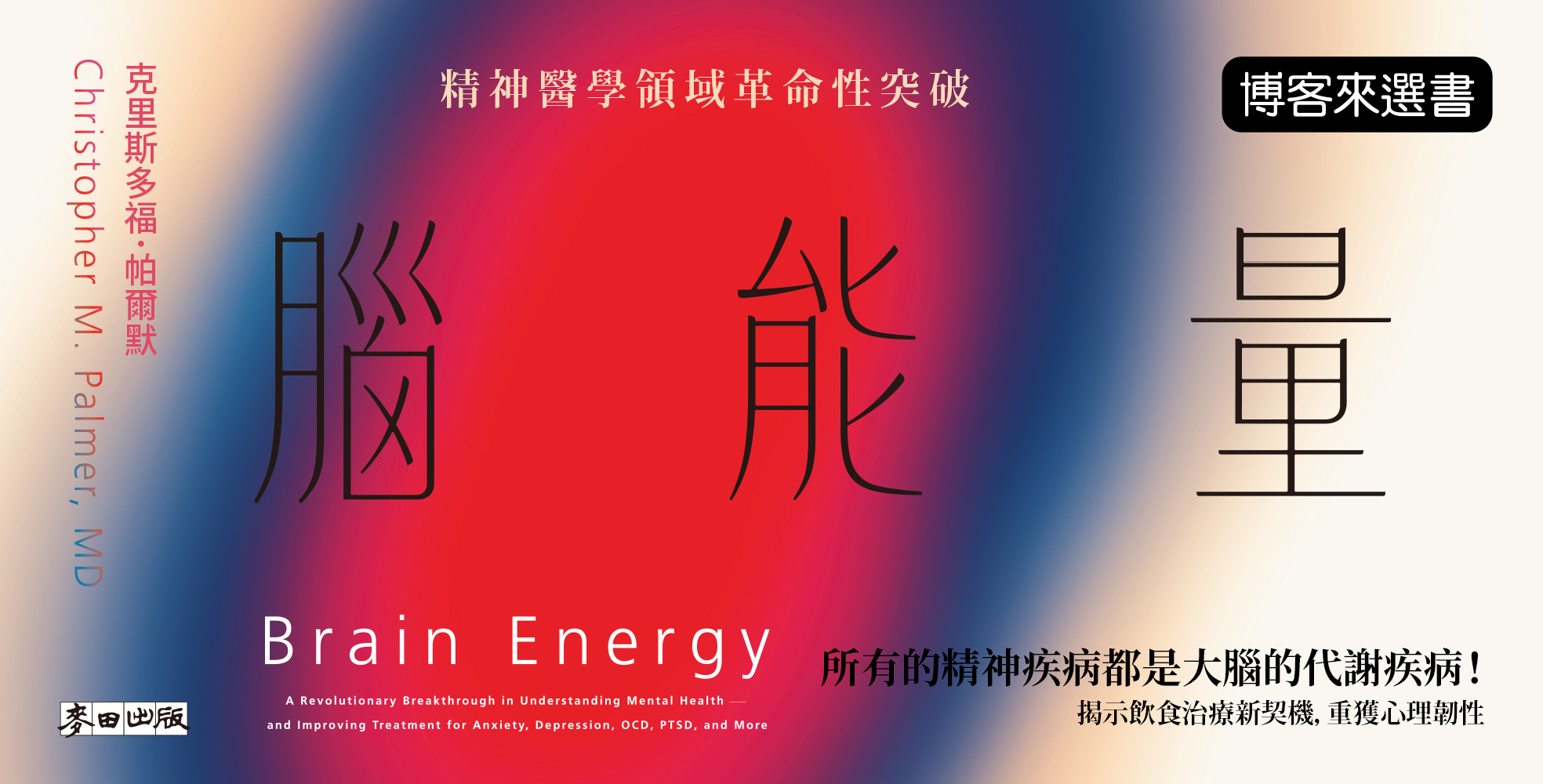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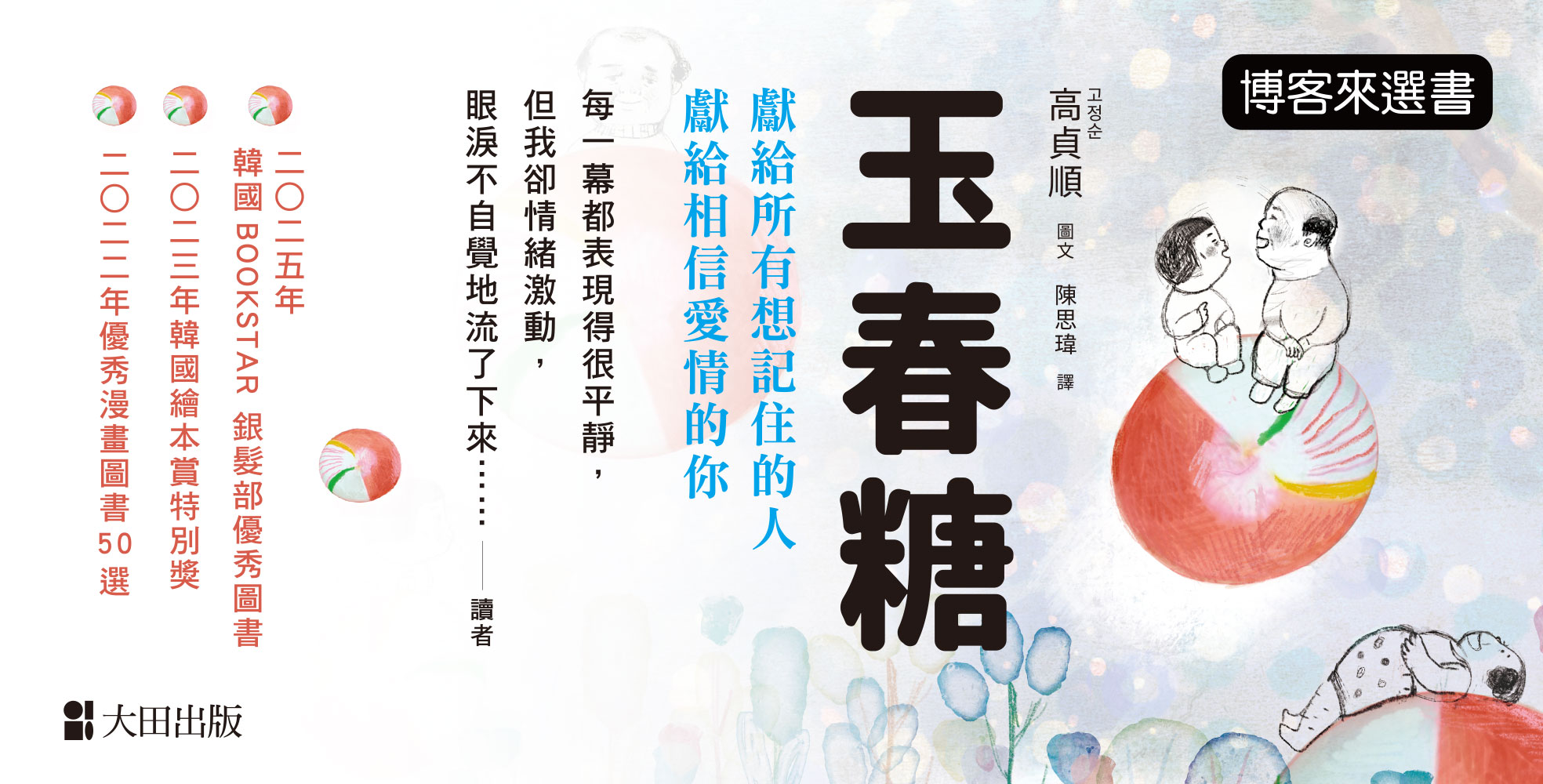

回文章列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