開始閱讀《尋找北極森林線》時,我人在蘭嶼。那是一個鋒面即將來臨的早晨,我鑽進朗島(Iraralay)附近的一座涼亭,打算在這裡消磨半天。隨著書頁展讀,不時抬頭眺望面前偌大的太平洋海域,不知不覺,空中雲層逐漸聚攏,海面上的「~」符號越來越多,我必須抓緊書頁,免得海風比我更倉促地翻讀。
起初一度懷疑自己帶錯了讀物。畢竟作者班.勞倫斯(Ben Rawlence)走訪的區域,和我所在的島嶼南轅北轍:蘇格蘭(北緯57度)、挪威(北緯69度)、俄國(北緯56度)、阿拉斯加(北緯67度)、加拿大(北緯63度)、格陵蘭(北緯61度)。北緯22度的蘭嶼介於北迴歸線和赤道間,我擔心作者在書中的報導和揭露,之於我是不折不扣的夏蟲語冰。
然而我多慮了。首先,書中揭露的北極圈區域,正年復一年走向無冰無雪的「綠化」階段。那遠不只是社群平台傳佈的北極熊失去冰山等畫面,勞倫斯自極地帶回來的,是更靜態卻更戲劇性的見證:原本不會出現在極地的樹種,正從南向北大舉移動,往逐漸消融的永凍層佔地生長。都說樹木不會移動,如今它們卻奮力突破邊疆,逃進逐年溫暖的北極圈棲住。「森林線」所指,正是這長久以來由冰河與森林構成的「森林—凍原生態推移帶」,正隨著氣候變遷不斷向北推進,速度從原本的一世紀幾公分,變成了每年幾百公尺。
倘若勞倫斯的尋訪調查和推論無誤,成為「氣候難民」的森林逃進北極圈,不只會造成激烈的生態擾動,也會與其他天候、人為因素聯手,加速永凍層崩解;一旦極圈冰河融化流入海洋,全球海平面可能上升達五十公尺——倘若這些成真,此刻我所置身的涼亭、早上沿路拍攝的芋頭田景觀、那些努力維持傳統樣貌的地下屋,還有瀕危樹種「琉球暗羅」僅存的一小片棲地……將全部化為海底遺跡。
▌全球暖化,極圈變成生物避難所
勞倫斯的上一本非虛構作品《荊棘之城》(City of Thorns),談的是非洲最大難民營達達布。從難民議題轉向森林及環境議題,勞倫斯曾在一場對談中提及,這並非寫作的重大轉向,「兩者都探討了人類如何在充滿不確定性的情況下生存,以及至關重要的是,在看似絕望的情況下,他們在哪裡找到希望。」
因而,這場2018至2020年間的尋找北極森林線之行,除了以六種標記森林線動盪變化的關鍵樹種——歐洲赤松(Pinus sylvestris)、毛樺(Betula pubescens)、落葉松(Larix gmelinii)、阿拉斯加雲杉(Picea glauca & Picea mariana)、香楊(Populus balsamifera)、格陵蘭花楸(Sorbus groenlandica)——為主角,勞倫斯也拜訪了各地的樹木、森林、生態學家,從他們長年的觀測與研究,提出氣候變遷對極地乃至全球的廣泛影響,以及可能的解方。
拜勞倫斯的報導能力、深厚的人文關照和開辦威爾斯黑山學院(Black Mountains College)的經驗,他以極優美流暢的文筆帶領讀者一同巡弋廣遼的近極圈城市和荒原,既能詳細摹寫本該成為老熟林的蘇格蘭松木山林,如何在長久殖民歷史的大量伐木、以及生態失衡的鹿群啃食樹苗等交錯影響下,成為母樹也難以為繼的「殭屍森林」;也能以人物描繪結合科學敘事,娓娓道來從蘇聯過渡到俄羅斯時期的科學家們,如何環繞著「落葉松」的樹木學、生態學、氣候與植被研究,推敲出落葉松是標記北方森林最能適應極地環境的指標物種,然而隨著北方針葉林的移動,包括亞馬遜雨林在內的南方森林,將在日益頻仍的野火、乾旱中,逐漸走向成為如非洲大草原般的稀木草原景觀。
依據這些科學家的研究,未來西伯利亞和格陵蘭等地區將會成為地球暖化的生物避難所,一名俄羅斯科學家甚至嚴肅提出了人類必須有移民火星的準備。而與樹木共享同一「氣候棲位」的人類,在諸多物種陸續北遷之際,又將在地緣政治的介入下,成為哪一種氣候難民?
▌警告:「森林很快就要來了」
然而,我認為真正令《尋找北極森林線》這本書具有擲地有聲之重量的,在於他以大量篇幅拜訪、敘寫的另一群人物——長久居住生活在凍原和森林邊緣、累積大量環境知識和文化的環極圈原住民(第一民族)。
這些族群包括曾住在大不列顛島的凱爾特人(Celt),分布在挪威、瑞典、芬蘭、俄國的薩米人(Sámi),西伯利亞原住民的其中一支恩加納桑人(Nganasan),阿拉斯加的科尤康人(Koyukon),居住在加拿大白楊河流域、管理傳統領域皮瑪希旺.阿奇(Pimachiowin Aki)的阿尼許納貝人(Anishnaabe)等。憑藉著長期與非洲原住民族群生活的經驗,以及各地的引路人協助,勞倫斯得以在環極圈人族的協助和指引下,親自拜訪分布在地球最北境的阿瑞瑪斯(Ary Mas)森林(歷經連續47個小時的無眠車震旅程!)也跟著阿尼許納貝族的耆老和青年一同滑著獨木舟「尋根」,來到白楊河畔的祖居地一起眺望極光,領略祖先知識的傳續。
這些環極圈民族和其他仰賴森林的物種一樣,同在第一線承受氣候變遷帶來的生存變異。與此同時,來自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的殖民也不斷洗去他們與自然的深厚關係。勞倫斯忠實記錄下的不只是拚命保存傳統知識的人們,也包括漸漸遺忘祖先口授,無動於衷地打開空調的人們——和你我一樣:「曼尼托巴人按下開關時,很可能沒想到這些支撐著他們舒適生活的水流,攜帶著連結流域森林土壤、河中魚類和海中鯨魚的印記。」
勞倫斯認為,這些在第一線的人與非人族群,握有地球全體生命存續的可能性。他記下不同原住民族看待樹、森林、魚、鹿等不同物種的各異觀點;也呼籲人們應往地質學、冰河學、樹輪年代學等,亦即大地存取記憶的物質當中,探求面對不確定未來的方法。他援引加拿大人類學家愛德華.孔恩(Eduardo Kohn)著作《森林如何思考》(How Forests Think),倡言人類當換位學習如森林一般思考。他在書末寫下的最後一句話,是我讀過所有關於森林的句子中,感受最為複雜的。
「森林很快就要來了。」
作者簡介
延伸閱讀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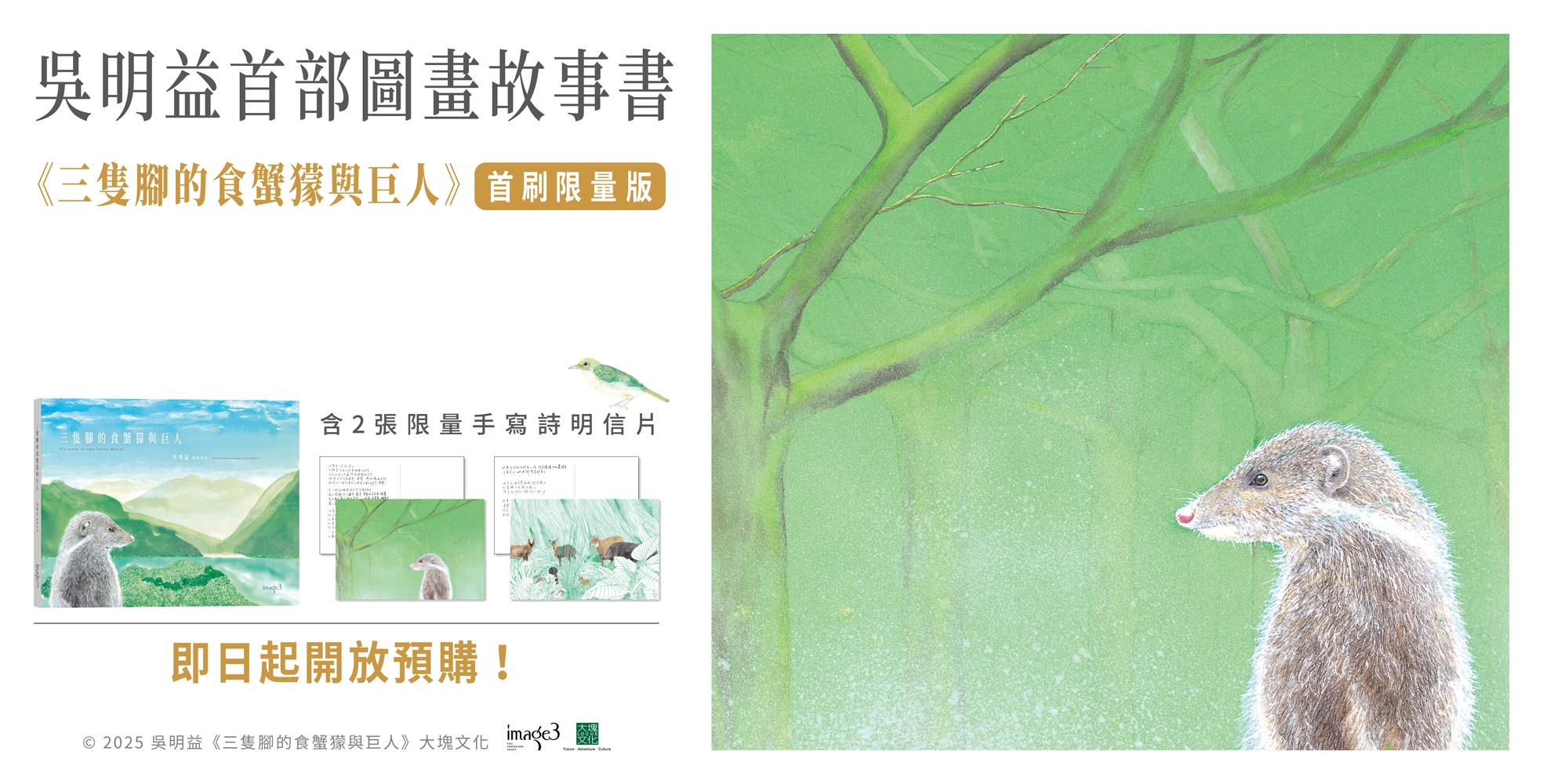









回文章列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