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終於脫離鬼地方了。
「《鬼地方》很悲。太悲傷了。」陳思宏說寫《鬼地方》的時候很痛苦,情緒太滿,幾度崩潰,「後來我想,可不可以把悲傷這件事情,用另外一個方式來呈現。」
那《社頭三姐妹》就是陳思宏對這問題的答案。
「我想要寫一本黑色喜劇。」陳思宏這回不寫鬼了,改請神。同樣寫悲傷,他改用荒謬的喜劇方式呈現。乩童世家三姐妹生懷異能,能通靈,偏偏本土X戰警在媒體亂象之前終究無法變成復仇者聯盟,小說中與神壇相對是政壇,真神假鬼,都在亂彈,而算命嘴糊瘰瘰(hôo-luì-luì),怎嘴得過網路謠言和媒體喇叭嘴。小小社頭縮影大臺灣,自古社頭多姓蕭,《社頭三姐妹》則是全民在起痟。「我想把宮廟跟神壇文化,還有『痟』這個字連在一起,所以寫成這本小說。」
一個起心動念讓小說家的創作列車轉向,離開永靖,下一站,社頭。
社頭在永靖隔壁,是陳思宏的大姊嫁過去的地方。可這一下筆,歷時四年。2020年有的構想,2024年才完成。四年車程,卡在哪裡?
「要讓人哭比較簡單,讓人笑很難,而且我不只是想讓人哈哈大笑,所謂黑色喜劇,既要抱持一種冷調,又要體現一種荒謬的質地,這個感覺真的很難抓。」小說家細數丟不掉的,還有自身堅持的文學性,怎麼結合腔調,怎麼跑情節,心頭惦記的要項大包小包,好不容易第一章寫完,後頭卻動不了。「直到我去了美國的永靖。愛荷華啦。一個小鄉下。」
陳思宏參加愛荷華駐村計畫,日子被活動塞滿。他注意到,有位高個子老先生場場來,但從不發言,就是老僧入定端坐在那。有一天,陳思宏在河邊遇到老先生,為什麼來聽呢?想聽什麼?那些答案都不太重要,重要的是,他瞄到老先生手上抱著一本厚厚的書,是但丁《神曲》。
《神曲》寫什麼?不就是詩人維吉爾帶著但丁遊地獄。令他想起小時候廟口善書,濟顛帶鸞生遊地獄天堂。那一瞬間,雲端破下一束光,腦袋瞬間清明。當晚陳思宏回到飯店,急沖沖把《社頭三姐妹》後續大綱寫下。
「《社頭三姐妹》的關鍵字,就是地獄。」陳思宏從小就愛看《地獄遊記》,喜歡裡頭對地獄的想像,剖心穿腸,挖眼割舌,觸目驚心的不只是刑罰,而是人間種種愚行與妄念的投射。「我覺得這世界上沒有天堂,這個人間就是地獄。旁人是地獄。」
不信天堂的男子以文學找到地獄直通車。一路高歌猛進,抵達了社頭,一本充滿地獄哏的小說誕生了。

如果你是《鬼地方》的讀者,應該早就窺見端倪。《鬼地方》裡的淑美「翻身趴在冰涼地板上,眼睛貼近地板裂縫,往裡面看,今天中元節鬼門開,她想,說不定可以瞧見地獄。」淑美想透過地板裂縫瞧見地獄,而陳思宏再用《社頭三姐妹》帶我們看見當代最新的地獄──傳統電視台、網路 youtuber、直播主進駐社頭,不是生活被鏡頭記錄,而是鏡頭反過來主宰生活。大到政壇罷免,小到店舖評價幾顆星,背後都有一雙看不見的手,若在古代,你可以說這是命運,是神之手操作一切,但《社頭三姐妹》讓我們清楚看到那隻手,正咖咖把鍵盤打出聲音來。
陳思宏說,「現在已經失控了,就算有人跟你查證,跟你講事實是什麼,你也聽不進去。在網路時代,我們失去了辯證的能力。我們活在一個後真相時代。」許多感悟或許從生活得來,畢竟他在臉書上什麼都講,生活很敞亮,自云紅得不知所以,分享「維力炸醬麵加巧克力超好吃」意外爆紅;也黑得莫名其妙,發文聲援李琴峰卻收到幾百封信要他去死。
他觀察,網路生態就是每個人都想要流量。踩人一頭,挑起爭端,負面的流量也是流量。「有時候你提出反對,反而讓對方的能量更巨大。」對小說家來說,這座新地獄的油鍋是用流量沖出來的,每個吃瓜群眾的怒火和熱情都可以拉高一點溫度,每一次回文,都是油鍋裡氣泡一聲啵。如果這地獄有針山,每一根針,都是一次點擊,被戳得越痛,就被釘得越高。高高捧起,才能狠狠殺下。
「所以後來我告訴自己,永不回應。」陳思宏說,「只要有人來罵我,我都會說我祝福你喔。」
等等,這聽起來不更像在罵人嗎?他呵呵笑著。「所以這個年代,小說家更重要,我們沒有辦法給答案,沒有辦法讓大家冷靜,但是我們可以把這個時代的瘋狂寫下來。」

最變形,可是最真實。《社頭三姐妹》既用黑色喜劇當哈哈鏡,也成為這個後真相時代的黑鏡。後網路時代是地獄,但前鄉土就不是地獄嗎?陳思宏不也把故鄉永靖叫成「鬼地方」?
「是啊,」陳思宏回得理直氣壯。「我為什麼離開永靖?就是因為我是 gay,我18歲那年離開彰化來到台北讀書,這才第一次變成我自己。從《鬼地方》到《社頭三姐妹》,我作品的核心概念就是,你的家人就是你的地獄,你來自什麼家庭會跟著你一輩子,我來自永靖,我一生都是永靖人。」永靖人初上台北,只想抹去一切,消除口音,不談過去,既是一個城市新鮮人,也是一個全新的人。
「你知道邱妙津出生在員林嗎?」小說家忽然對我發起突襲,我搖搖頭。腦中直覺浮現邱妙津履歷,天才少女,北一女,台大畢業,巴黎深造。一直以為邱妙津是台北人。「邱妙津跟我一樣讀永靖國小,後來我才發現,其實她的父親是我以前的國小老師,所以我們在同一個空間裡面相處過,但她的小說跟遺書從來沒有提過彰化。如果此刻邱妙津還活著,一定開始寫彰化了。」小說家指認出同鄉,不如說是指認出另一個脫出地獄的同伴。「來到中年以後,我終於有勇氣跟精力去面對我的故鄉,正是這些過去的痛苦,會幫助你的書寫成熟。我也終於敢坦承,我是一個鄉下人。」
說起來,年紀也是地獄。沒有不怕老的gay。少年思春,中年思宏,紅起來的思宏回頭,發現正是那些讓他痛苦的,才是他想對話的。但陳思宏不改大炮性格,「寫《社頭三姐妹》的時候,我心裡面第一個念頭就是,我必須跟社頭說對不起。我寫原鄉,絕對不歌功頌德。那些犯罪啦、邪惡啦,城市能夠發生的事情,鄉下可以用好幾倍速來發生。」
那就是《社頭三姐妹》最好看的地方。小鄉鎮被他寫成壓力鍋,放在臺灣島上可能要幾年才催生的事情——例如推倒一個領袖,弄壞幾個人的人生——但在社頭,一切加速,馬奎斯的馬康多尚且百年孤寂,陳思宏的社頭則一頁十年。小說劇情加速造成喜劇,人物心境慢速燉成悲劇,悲喜交織,哭之笑之,那不是地獄是什麼?
也是這樣的地獄,讓人想離開,卻離不開。打算回去,偏回不去。陳思宏像是希臘和日本神話都有的,離開地獄前被交代不能回頭的男人,偏偏就是那一回首,成了小說。陳思宏下筆抓住那瞬間。

但為什麼是社頭?「我大姊嫁去社頭,我從永靖騎腳踏車過去,五分鐘就到了。」對陳思宏來說,那五分鐘的「距離」很重要,《鬼地方》寫永靖,離自己太近所以身心疲倦,「可是社頭跟我有一個距離,這給了我安全感。於是你說它壞話,可以說得更爽快一點、更歡樂一點。我很需要一個東西叫做冷眼旁觀,這讓我寫這本書的時候比較放得開。」
距離拉遠了,故事放開了,卻依然秉持從《鬼地方》以來的優良傳統,《社頭三姐妹》一樣有米粒那麼多的人物,但誰是誰,臉譜強烈,粒粒分明。說什麼話,拿什麼腔,都不會糊。問他怎麼寫作?陳思宏不藏私,不知是否因為戲劇所畢業,他給了四個字,「方法演技。」他說自己有一個小本本,一個角色吃什麼用什麼穿什麼,有什麼童年、說什麼話,清清楚楚,他甚至會幫人物畫像。人物完成了,第二步驟是扮演他,變成他,用他的方式思考,用他的方式講話,乃至,覺得自己就是他,「例如,我知道明天早上要開始寫三姐妹裡二姐的章節,我去睡覺,可是真的在凌晨四點半左右,我耳邊會聽到二姐跟我說話:你該起床囉,該寫我囉。」
是神來之筆還是鬼壓床?是小說家在創造角色,還是角色在附身小說家?《社頭三姐妹》寫神乩之舞,但陳思宏的寫作從來是在降乩。小說裡,神通難敵媒體,超能力不及網路算力,亂哄哄臺灣,你方唱罷我登場。在這個活地獄裡,三姐妹的設置有其玄機,大姐通靈眼,能看見未來,二姐好鼻師,能聞出身世,三妹神通耳,能聽心聲。姑且不論超能力,但是眼能觀,鼻常嗅,耳多聞,陳思宏說,「這三個能力,就是此刻很多人已經失去的能力。」
他說在捷運上聞到臭味,車廂裡有人拎著一袋發臭的塑膠袋,但沒人有反應,失去了嗅覺,乘客的眼睛都鎖在一方手機螢幕裡。失去感知,是地獄的罪,還是地獄給我們的懲罰?那《社頭三姐妹》也是網路時代的罪與罰了。
凝視深淵的人,也被深淵凝視。在陳思宏筆下,他人即地獄的最新版本是網路公審、謠言和虛擬社群生態,這一切都盛裝在你的小小手機裡,我們觀看別人,也被別人觀看。凝視地獄的人,是不是凝視地獄凝視著你凝視著地獄⋯⋯一個無限套環。他的小說正是點出這個結構,地獄的製造法。
「要是你是創作者,我會建議你盡量不要帶抗噪耳機。因為所有噪音都是你的創作。我會戴著耳機,可是沒有開降噪,也沒有聽音樂。」陳思宏發現只要戴著耳機,別人在他面前就旁若無人,照講家務事。小說家面不改色,內心咋舌,大大方方的聽,忙不更迭的偷。也是一種冷眼了。既抽離,又介入。三姐妹的超能力何嘗不作如是觀?
這麼說起來,《社頭三姐妹》其實情感濃度不下《鬼地方》,正如小說書名出現的數字——三個主人翁——三倍的傷害,三倍的死亡,三倍的悲傷。「我想把它沖淡,我的確花了很大力氣去把它沖淡,用更荒謬的場面來面對死亡這件事情。」這麼濃,卻被沖淡了,原來好小說往往是從距離中誕生。怎麼稍微拉開一點,反而讓故事更進去了。永靖到社頭的距離,那五分鐘,成就了陳思宏寫作最好的時候。

延伸閱讀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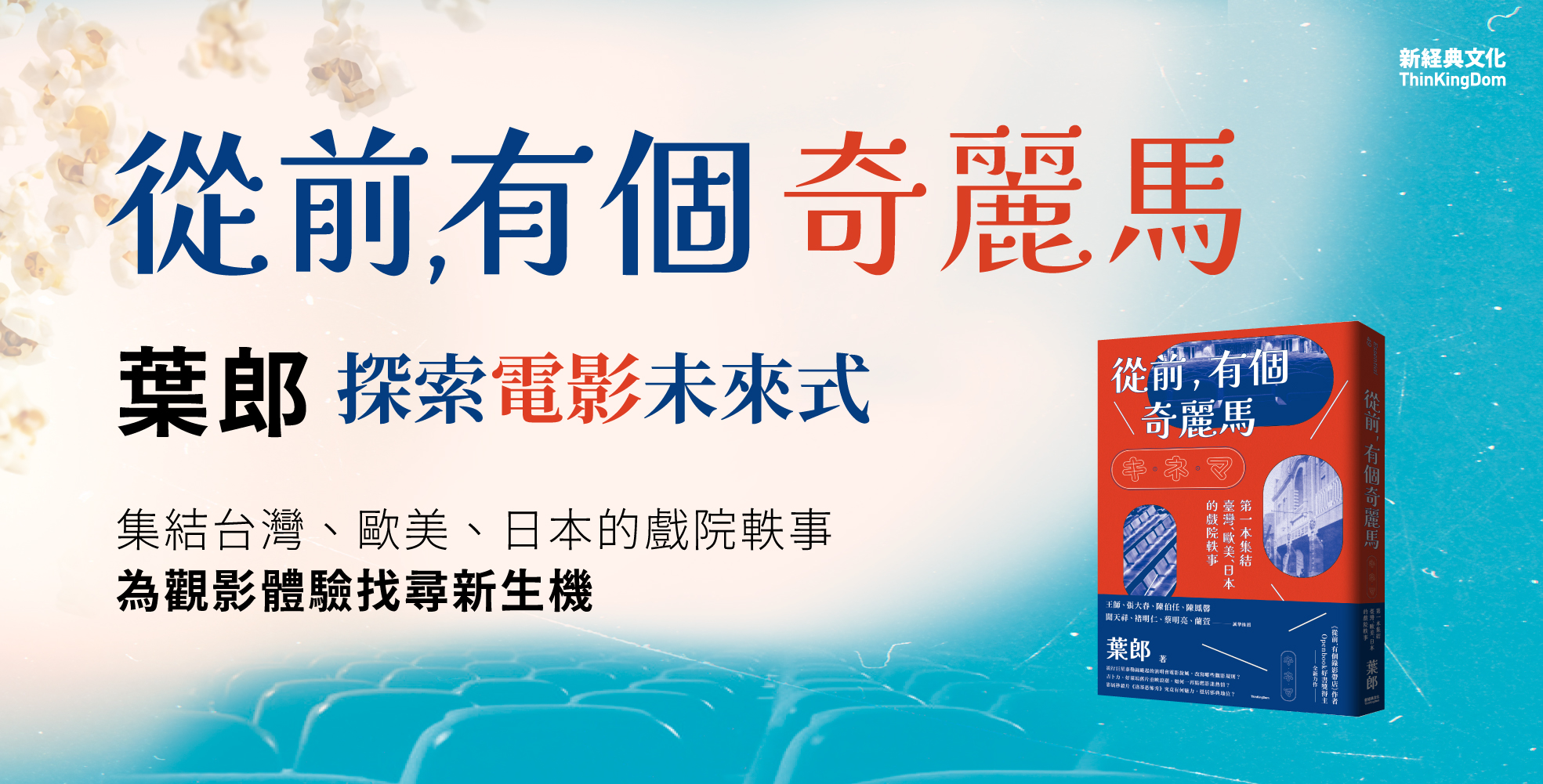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回文章列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