 改編自美國著名小說家傑佛瑞尤金尼德斯的同名作品,也是《愛情不用翻譯》、《凡爾賽拜金女》、《貓王與我》蘇菲亞柯波拉(Sofia Coppola)一鳴驚人之作,以陰鬱籠罩下的情竇初開,精準描繪當代青少年的不安、徬徨與孤獨空虛。(圖/東昊影業提供)
改編自美國著名小說家傑佛瑞尤金尼德斯的同名作品,也是《愛情不用翻譯》、《凡爾賽拜金女》、《貓王與我》蘇菲亞柯波拉(Sofia Coppola)一鳴驚人之作,以陰鬱籠罩下的情竇初開,精準描繪當代青少年的不安、徬徨與孤獨空虛。(圖/東昊影業提供)
我發現將作品與事件當魔術方塊看,每次看就會有不同發現。
比方從人心來看那些回憶的流變,或從事件中鑽個小孔來看人性的切面,這對我來講都是生之樂趣,
它不見得會接近真相,但比較接近我人生想追的真理。
如果電影大師塔可夫斯基說當個「合格的讀者」是重要的,那我們何妨一路當個找答案的人,
在找答案的過程中,它就是你自己的故事了。
※本文可能有劇透,請斟酌閱讀※  電影中的花季少女都活成了童話中的女主角充滿了死亡的意象,在森林如夜幕的秩序中,她們亮眼的青春像是命運的獵物,難以有自己的名字,在前方等待她們的是壯盛青春成了中產家庭窗前植栽的本身,以死亡週期性來象徵他人與社會的體面。
電影中的花季少女都活成了童話中的女主角充滿了死亡的意象,在森林如夜幕的秩序中,她們亮眼的青春像是命運的獵物,難以有自己的名字,在前方等待她們的是壯盛青春成了中產家庭窗前植栽的本身,以死亡週期性來象徵他人與社會的體面。
蘇菲亞柯波拉導演的電影總充滿了意象,且特別的是她所隱喻的並不過時。以這部《死亡日記》(也曾被翻譯為《處女之死》來說),一開始潔白的社區、大群衣著體面的大人、漾著粉紅色調的物件,與如花般的里斯本家四姊妹在周圍男性視角下從車上下來,那樣燦爛如朝陽的肉體意象,如精確地被放在精緻的娃娃屋玩具裡,不知為何給觀眾的印象像是曾沾手的口香糖、被咬扁的彩色吸管、曾經熱香的爆米花。當「滿開的青春」被放在其中一角時,如同一種「擱置」、「等待」的意象,進入了精裝版的世界,有了保鮮膜的窒息,顏色還是透亮的,膜下物的色彩卻讓人窒息。
與其說這部電影在講四姊妹如何不適應強力的「規訓」家庭而折損,更像是電影裡活動的人,都活在一種充滿假像,為自己身分而活的死亡陰影裡。蘇菲亞柯波拉非常擅長以滿滿物件的世界,來表達許多人是活如「蝴蝶標本」的生之處境。像是「死亡」的招喚原本就是現代化城鎮前進的另種趨動力。
這點在是枝裕和的《無人知曉的夏日清晨》以不同顏色的包裝零食紙,來進入滾輪一般的囫圇人生,表達出城市這系統如何以璀璨的無機來催熟我們的感官,讓其成為一種「開到荼蘼花事了」後的浪擲與感傷。王家衛的《重慶森林》也將壯盛的青春放在如保鮮盒的方寸地,飛不出去的意象跟其中彩色飲料攤相呼應,塑膠感城市在我們呼吸之間,不覺成了生如迷宮的回音。
《死亡日記》也是這麼美的電影,以鮮豔生命與無機世界作抗衡,其中的大人們崇拜秩序到雖生猶死的狀態,像忘記了自己的年少如何像莽原上要遷徙的動物般躁動,那期間充滿了等待「預備備」的茫然與興奮。然而被放在電影中高級社區裡就如同被插進花瓶的花苞,預約盛開是為了家中的體面,也同時在花苞時就可以想像死亡的周期。
 (圖/東昊影業提供)
(圖/東昊影業提供)
這整部片是大人過度崇拜秩序的代價,他們從始至終像是某種信徒的無意識,大人們崇拜著這樣的盒裝文明。如同80年代末曾經到處都是一整排制服空姐的廣告,標準笑容與制服,象徵著完美的世界將起飛,而里斯本姊妹被當成群化的目標被幻想,那鮮豔花色的裙擺與金髮,與其說她們是哪一個更有魅力,不如說她們因從屬於自己的背景與中產家庭,而被理所當然(包含暗戀她們的男孩視角)被放在一個花瓶裡,成為四朵花骨而非是鮮活的人。
因此她們的死亡日記不是從死亡那刻開始,而是意識到自己處在「標本」處境下的倒數計時。一開始是從最小的13歲女兒塞西莉亞如同生物直覺般地想自殺,她像一隻誤飛進房子的鳥下意識飛竄找天空,虛實間來回遊蕩,最後力竭而死般。近乎是她潛意識感到受困,有如蘇菲亞柯波拉另一部作品《愛情,不用翻譯》中女孩走在陌生城市,也意識到在大落地窗內的自己如此鄰近自由,但自由也像個展覽品,與青春同時標價在牆上展示。她們的青春除了展示的功能,卻不代表有源源的生命力。
 (圖/東昊影業提供)
(圖/東昊影業提供)
而在里斯本家排行老四的拉克絲最具反抗意識,始終在做困獸之鬥,有如一縷鮮活於水泥秩序中。在畫面上既衝突又美麗,她企圖在完成自己個人的小史詩、長期徒勞的奮鬥,看她如同在百貨櫥窗中看到美人魚的奮力一遊,原本想以愛情來驅動自己的反抗,然而在一場畢業舞會與野砲後,她也如美人魚獨自醒來。畫面俯瞰,她是如此小小一個在無邊的草皮上,朝露未散,她昨晚如夢的洋裝與小皇冠還提醒著她有一夜的自由,隔天的綠草如茵卻是一點生機也沒給。
整部電影裡AIR樂團的電音撒下如夢的虛幻感。夢隨著電子如此易冷,拉克絲喜歡的搖滾是她僅存的一抹血性。里斯本姊妹渴求的都如沙漠之水,如遠方寄來的旅遊誌、跟男孩們求救時電話那頭傳來的搖滾歌曲,他們都活成童話中的女孩充滿了死亡的意象(如《長髮公主》那不可能的高塔求救,且人只剩長髮記憶的模糊、《睡美人》與《白雪公主》藉由死亡的遁逃、《美人魚》渴求別人的記憶點卻如浪花)。她們像是都沒有自己的名字,更多的是青春壯盛成了植栽的本身。
於是她們哭著圍著一棵要被砍掉的榆樹也是隱喻,大人跟她們說這棵不砍掉整排樹都會生病,彷彿青少年問題如果不解決一兩個,整個都會生病一般,她們再美也被當成一整批,就像前述的童話少女都只是被當成慾望的象徵而非她們個人一般。
青春期如電影名作《四百擊》結尾一樣是有著封閉型盡頭的預設,《四百擊》的主角安瑞直言要說假話大人才會相信。因為當你說了假話就代表你服從了這個秩序本身,真假反而不重要了。最後里斯本太太說她不懂,她明明就很愛這四姊妹,但她的愛卻比死還冷,畢竟過度的秩序膜拜的是死亡本身,她本身就活成了無愛的象徵。
如同童話裡總是天羅地網的秩序與制度,只是它們都以森林的黑夜一般灑下,卻沒有作者為故事裡女孩描述黑夜裡的星星。
如電影中的大人除了地位沒有在愛任何一件事,於是電影中最後一場上流派對這麼絢爛也寥落,喜愛過里斯本姊妹的男孩即將長大,他們的成年禮是更愛地位與秩序,以及即將因過度秩序下,犯下輕慢這世界的愚行(對照如今日普遍的政治與金融問題)。
「青春」在大量被商品化後,總會有幾個替罪羊,他們除了被戀慕的青春外並不能留下什麼,像里斯本姊妹成為長大的人的「傳說」,以及後青春期的證據。「青春」也是種倖存,它可能成為你日後活血的勇氣,也可能只是沒有盡頭的海岸線而已。
蘇菲亞柯波拉導演下的女性有如Edward Hopper畫中女性的甦醒與開門接力,無論《死亡日記》、《愛情,不用翻譯》或是描寫瑪麗皇后的《凡爾賽拜金女》,在物品可以擁有人與代言人的世界,她們在高牆內與厚實城堡中的絮語迴盪,交棒彼此的命運。一般來講階級可以某種程度保護女性,但同時也要求妳扮演好自己的身分。如同廣告中的少女通常提供巨大的元氣,一代接一代是那麼地相似,彷彿這世界一直有死亡在追趕著我們。
每一幕廣告她們既是蝴蝶也有著前一代被作成標本的記憶。《死亡日記》其實正是世世代代被反覆翻閱的少女日記。
※本篇文章由作者個人創作授權刊登※
《死亡日記》(The virgin suicides)
導演蘇菲亞柯波拉一鳴驚人的出道之作,克絲汀鄧斯特、喬許哈奈特主演,這部電影細膩描繪了少男少女的私密心事,入選1999年坎城影展導演雙週單元、2000年法國電影筆記年度十大影片。最近重回院線,其美學值得大銀幕觀賞。
作者簡介
「你花最多時間的,終會變成你。」
──
音樂迷、電影痴,其實背後動機為嗜讀人性。娛樂線採訪與編輯資歷二十餘年,持續觀察電影與音樂;現為自由文字工作者,從事專欄筆耕。 曾任金曲獎流行類評審、金鐘獎評審、金馬獎評審、金音獎評審、中國時報娛樂周報十大國語流行專輯評審、海洋音樂祭評審、AMP 音樂推動者大獎評審。樂評、影評、散文書寫散見於報章雜誌如《中國時報》娛樂周報、《聯合報》、《GQ》、《幼獅文藝》,及「博客來 OKAPI」、「非常木蘭」、「書評書目」等網站,並於「鏡好聽」平台開設Podcast 節目《馬欣的療癒暗房》。
著有:散文集《看似很美,其實是壞掉的》、《邊緣人手記》、《階級病院》;影評集《當代寂寞考》、《反派的力量》、《長夜之光》、《看似很美,其實是壞掉的》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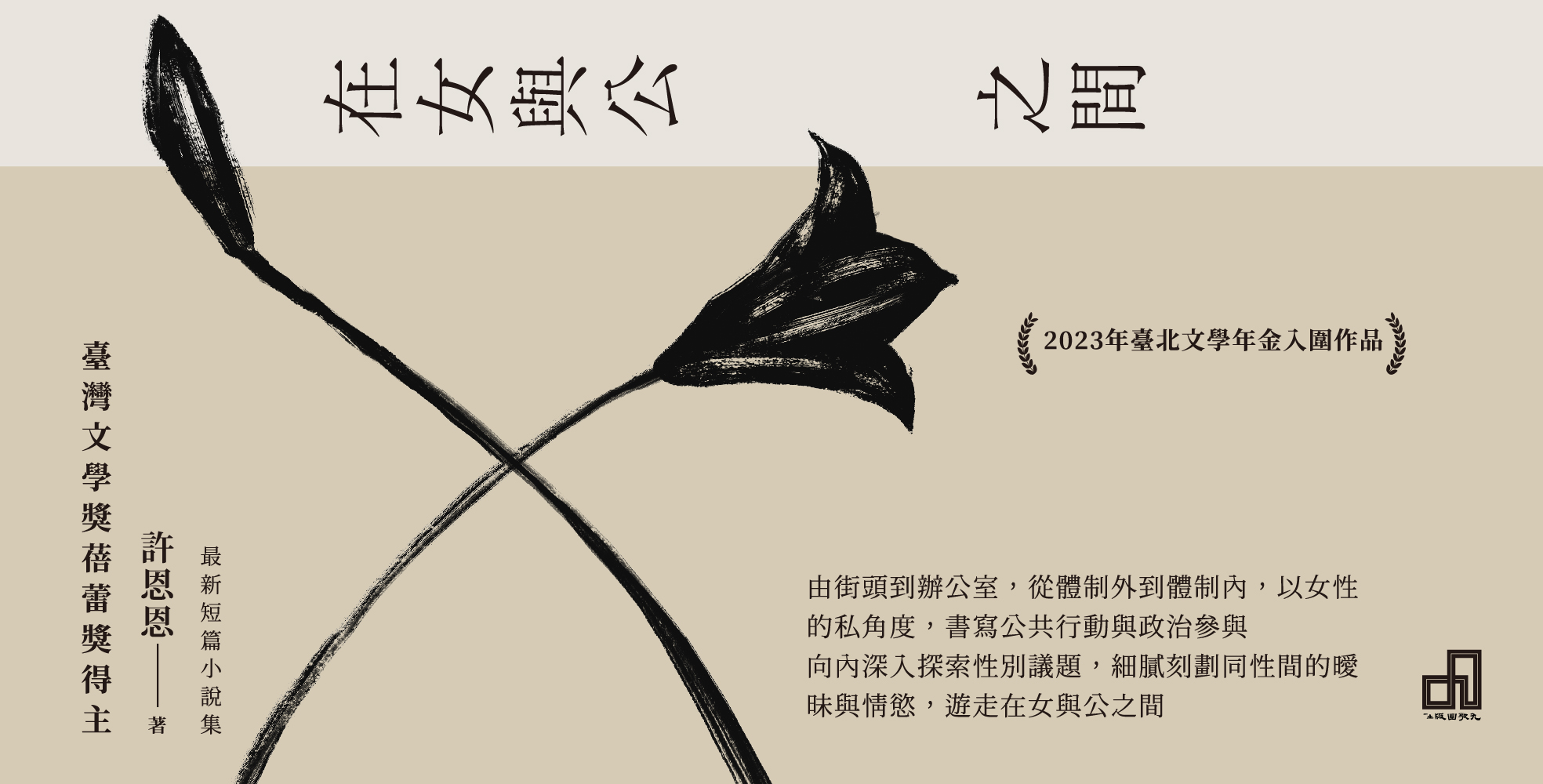









回文章列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