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9年,記者約翰.葛里芬(John Griffin)為調查南方種族隔離真相,運用藥劑將自己染黑,佯裝成黑人,前往南方跨州旅行。
數周旅程中,一個迥異於他印象的南方浮現眼前:白人櫃台人員僅因他的外表便粗聲惡氣,衣冠楚楚的駕駛在他搭便車時口出穢褻,無來由地恫嚇他,仇恨的眼光在各州無處不在。葛里芬領悟,這個長久屹立的體制,是由眼神、表情、動作砌築的流動監獄,將黑人困在深切的孤立中。白人的憎惡毫無來由,一切僅是因著他染黑的膚表。
而這些細微的歧異,是他以白人形象出現時無法體會的。更替膚色,其實也更替了他一雙眼,讓他見到白人隱藏的殘暴面向,罪惡曝白,恥辱炭灼,歧視作為綿密而全面的體系,在日常生活中細膩運作,滲透至人們骨髓深處,使他寫就《像我一樣黑》(Black Like me)一書。
看,有時如葛里芬,曾因視野障蔽,難以洞悉結構全貌,有時卻如《鎳克爾男孩》(The Nickle Boys)主角埃爾伍德,在半明半昧中探索,從朦朧裡窺見真實。
黑人男孩埃爾伍德成長於六〇年代,彼時如約翰.葛里芬這般關心黑白種族議題的社運分子,在全美熱烈宣講,發起大規模抗爭,而馬丁.路德.金恩牧師(Martin Luther King, Jr.)的知名演說,更是鼓舞了廣大黑人群眾。埃爾伍德自小深受民權思潮的洗禮,原本可望以優秀成績升上大學,脫離家鄉的貧困社區,加入大學生遊行示威的熱血行列,卻陰錯陽差被送入鎳克爾矯正學校。
作者科爾森.懷特黑德筆下的鎳克爾學校與學童遭遇,在歷史上真有所本,而他安排埃爾伍德進入這間封閉機構,宛如濃縮了美國壓迫黑奴的歷史。學校不僅在校內實行黑白隔離政策,且對黑人學童施加私刑,而校方高層亦與當地權貴合作,假借就業訓練名義,剝削黑人學生勞力(是否令人聯想台灣某些學校?)埃爾伍德發現,儘管1964年美國國會已通過《民權法案》,禁止因種族、膚色產生的歧視行為,他嚮往的公義社會,仍只存在於書刊報紙上。適應鎳克爾生活後,他生出一雙嶄新的眼睛,於黑暗中看清現實輪廓,目睹自身與同儕因無止盡的詈罵與痛懲,意志消磨殆盡,淪為馴順奴隸。隨著埃爾伍德將目光由外轉內,他的精神逐步萎縮,從對外頭自由世界滿懷希望,爾後只求免於餓餒傷殘,小說氛圍也漸次收窄,愈發令人窒息。
法律定義黑人為人,但在法律所不及之處,如鎳克爾這般封閉機構,黑人不是人。法規僅是種族主義體系的外層支撐,即便換了一套法律,南方蓄奴歷史遺留的深刻歧視,這個由經濟、政治及至於心理各方面架構起的主從體制,依舊屹立不倒,白人對黑人群體的憎惡與排除,如同呼吸般自然。優勢者一聲輕蔑的哼嗤,橫暴的壓迫與體罰,整體社區對惡行的默許,都是體制的一部分,一遍遍刮削鎳克爾男孩的人格,令他們只餘絕望麻木,成為體系間隙填塞的渣屑。
鎳克爾男孩不是人,就如學校名字暗示,他們只值五分錢(Nickle亦為五分錢之意)。
然而埃爾伍德沒忘卻他熱愛閱讀的倡議文章,尤其是金恩牧師演講唱片高昂的語調:「……我們會用我們承受苦難的能力讓你們屈服,總有一天我們會贏得自由。」埃爾伍德仍想當個人。
當現實不是穩妥的一日三餐,而是殘羹冷炙,隨時可能迸發危機,竭盡全力只為避免受暴,人是否能相信未來會有更好的許諾?在肉體到精神漸進的打擊下,其餘鎳克爾男孩不是死於非命,便是斲喪意志,只要校方略施蠅頭小利,便如他們的祖輩,認分地混沌度日。埃爾伍德卻始終企圖保有尊嚴,與同儕形成鮮明對照,而他在無助中,清楚認識到他要對抗的不僅是這所矯正學校,而是龐大悠久的體制、建構體系的廣袤地域,甚至整個國度的蓄奴痛史。
作者最後運用切換敘事時序,埋下線索,逐漸揭露身分真相,製造出小說高潮——當人懷抱著信念,清醒地孤注一擲,現實卻以最不可測的方式,坦露體制的荒謬,而惡意以親切的面貌環伺在側,直到某一刻才顯現出來。種族主義最深刻的惡,在於不僅鎳克爾男孩在體制中不是人,體制中看似尋常的普通白人,其實也受其催動,激發出遺傳自奴隸主祖先血脈的殘暴,失去人性,化為殺戮的器械。
這是種族主義最大的邪惡,將所有人都扭曲為非人,而個體間只存在著壓迫與屈從,主與奴,宰制與被宰制。
埃爾伍德的反抗沒有成功,他沒能成為嚮往的民權英雄,上帝將命運的骰子拋進無光的角落。然而,作為鎳克爾無聲受害者的化身,他決心反擊整個體制的舉動,使他被還原為人,透過同伴,將他的不幸轉化為遺緒,乃至於在數十載後,他的經歷得以同鎳克爾學校過往出土,成為彼時南方黑暗歷史的跡證。
而那是他睜亮眼睛所見的,報章雜誌公共輿論所不得見的真實。
埃爾伍德在極端絕望的情境下,選擇了與不公義對抗。他不僅犧牲了,而且犧牲得無聲無息,無法如偶像金恩牧師,成為一名壯烈的殉道者。至最後一刻,他仍是一名微小的,被侮辱與損害的,鎳克爾男孩。
但他或許是唯一一名,像他一樣黑的少年,能夠在多年之後,被痛苦地記起姓名,關於他的回憶被探掘見日,無法抹拭。為此即便逝去,他也已成為一個人,許久以前。
作者簡介
延伸閱讀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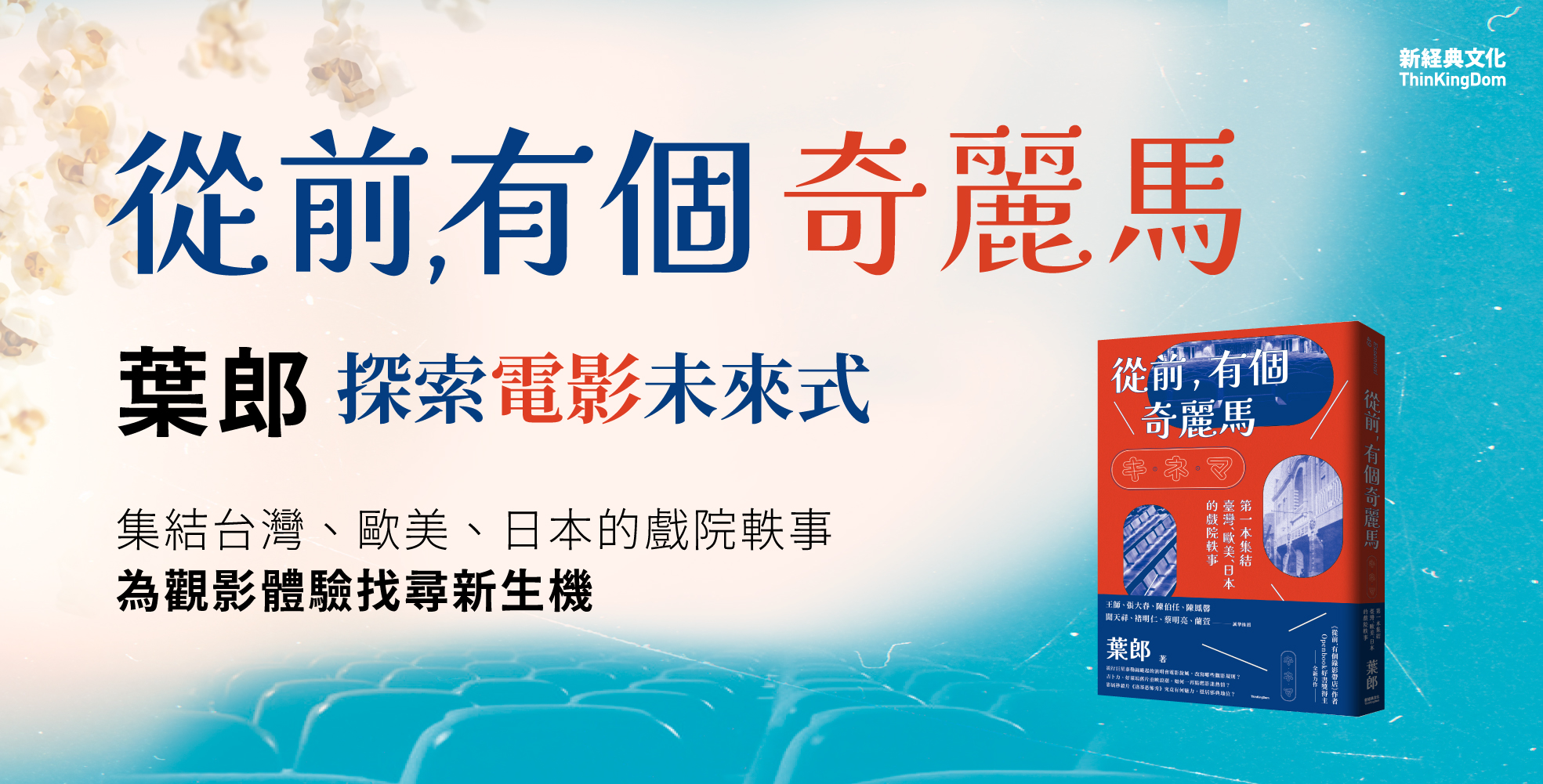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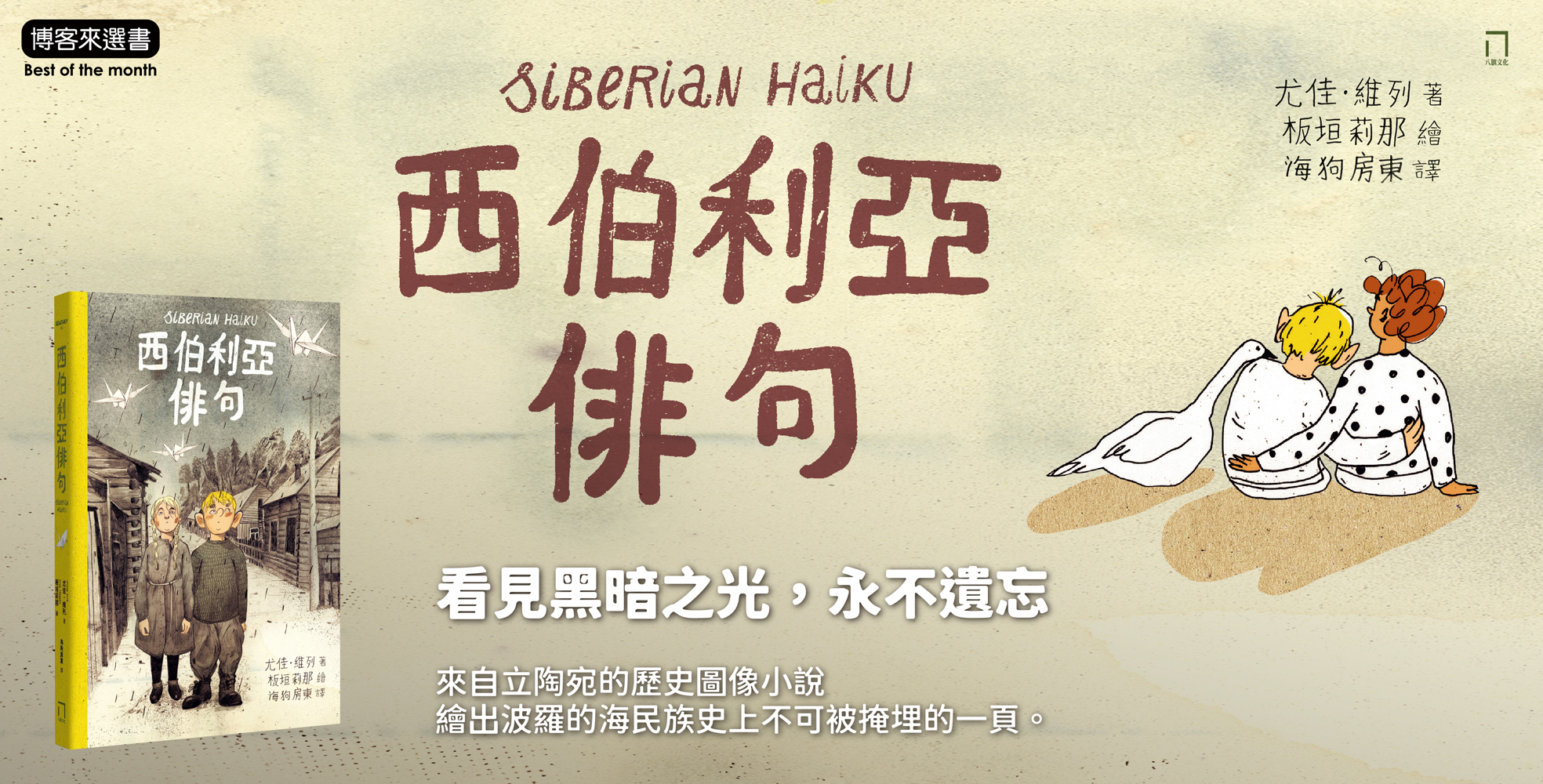






回文章列表